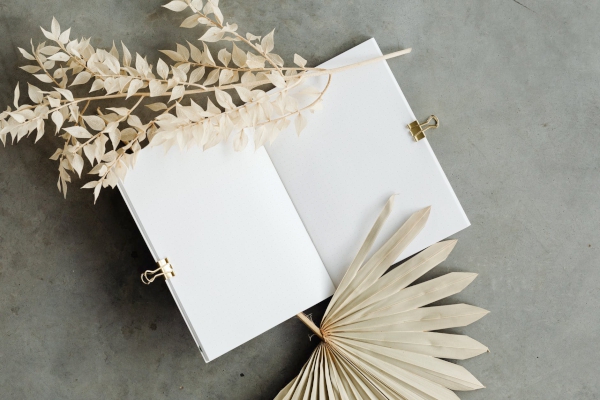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协议书(精选32篇)
2、发包方的权利
(1)承包金的收取权
土地承包金是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由承包方向发包方交纳的作为使用承包土地的对价的费用。在土地租税制度改革以前,通过均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只须向发包方交纳乡统筹和村提留即可,无须另行交纳承包金。换言之,承包金是以乡统筹和村提留的形式收取的。而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则应支付承包金。
(2)调整土地的权利
村集体是否拥有此项权利,视土地承包模式有
所不同。在均田承包模式中,村集体一般均有权对土地的分配进行调整,在规模经营和股份合作模式中,村集体甚至有权将土地收回重新发包,而在湄潭模式中,村集体则不具有调整土地的权利。
当然,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利很大程度上受到村民意愿的左右,除了少数集体领导人违背村民意愿的情况外,多数情况下是集体与村民共同的选择。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三、制度的困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农业的经济结构、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来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制度在在前一阶段中释放出来的效率,但是它在运行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矛盾,陷入了制度的困境。
(一)合同主体模糊
《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但是,集体究竟是指乡(镇)级、村级还是村内集体经济组织,则比较含糊。这直接导致两个后果:第一,本来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发包方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承包方自觉按照合同的约定用途使用承包的土地,但是由于法律没有对发包方到底是哪一级农民集体作出明确的规定,结果导致承包方随意变更土地用途的情形放任自流。第二,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应为集体经济组织,但是由于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农民缺乏行使集体所有权的组织形式和程序,甚至缺乏行使所有权的动机。少数干部凭借集体所有权,或任意摊派,加重农民负担,或任意处分土地,造成大量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或以权谋私,导致土地使用的分配不公。这已成为导致耕地严重流失,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承包方的资格问题,即谁有权与发包方订立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是以农民个体还是农户为承包方?其二,承包主体是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还是打破这一界限,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通过承包合同取得土地使用权?如果承包方的资格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权的实现,危及公平原则的贯彻。
(二)合同关系不稳定
传统理论认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自然拥有土地承包权利。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
我国《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都规定,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这里的“村农民集体”可以理解为全村农民人口,当然包括新出生的人口在内。这样,村农民集体成员的界限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如果农村土地的分配随着成员数量的'变动而变动,频繁调整承包土地直接影响到政策的稳定和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容易引发农业用地经营中的短期经营行为。另一方面,我国农民的耕地面积本来就已经非常有限,如果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不断调整,非要平均化,势必使目前超小规模的承包土地继续零碎化,不便耕作,影响水利设施和农业机械化的合理使用,使科学技术的推广受到限制,经济效益下降。
(三)合同权利义务失衡
由于在承包合同中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谈判地位是不对等的,承包方几乎没有多少发言权,合同条款大部分由发包方事先拟定,
承包方只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事实上,农民的生活保障基本依赖于农村的土地,不得不对全部合同条款一一接受。承包经营合同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表现在:首先,几乎村集体作为发包方除了进行统一经营这样一些法律约束力较弱的义务外,几乎不负什么义务,而农户除了负有对于因为农地而产生的义务外还附加了三提、五统、两工等义务。其次,发包方拥有过大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农民肩负的承包义务过重,违约的事由范围也就过大,往往无法按时全部履行,发包方动辄以承包方违约为由解除合同或以解除合同相要挟。即使承包方没有违约,发包方也会以规模经营为借口收回土地然后重新高价发包,或者以公共建设为名非法征用承包的土地,而承包方却没有任何对抗的权利。最后,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却无法自由转让、转包、抵押,因为发包方是否同意成为承包经营权能否得以流转的关键。结果,承包方所获得的承包经营权难以成为一项完整的财产权。
(四)权利义务不明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一般只要求承包方交纳国家、集体的税金、提留、承包费,完成粮油定购任务和义务工的约定,但对各个项目的数量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定。村提留、乡统筹往往由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自行决定,缺乏法律和第三方制约。近年来,各地又因修建学校和地方公共设施,任意摊派集资,下达义务工任务,层层加码,形成所谓“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负担重就重在统筹提留、义务工、集资摊派罚款上面,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更为严重的是,土地分包是采用行政分配的方式,多数情况下,连承包合同都不存在,许多承包合同中的事项完全由村社来规定,或者说由习惯法来规范,承包方不清楚自己需要承担的义务到底有哪些,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否遭到侵犯。
随着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最后期限的陆续到来和第二轮承包合同的续签,如何对原来的承包合同制度进行完善,实在是摆在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制度构建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讨论,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承包方所获得的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是物权还是债权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还不是完全的物权性质的权利,应予以物权化。对物权化的思路我不反对,但是,是否只需在物权法中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就万事大吉、不需要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进行规范了呢?我认为,即使物权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能排除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进行规定的必要性。理由如下:
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设立作为物权的承包经营权的基本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是直接依法律规定取得的,需要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签订承包合同。即使在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和期限法定化以后,也仍然需要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承包合同确定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使法定的抽象的权利规定具体化。事实上,在承包合同关系发生纠纷后,法院都是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加以处理的,合同法是保障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的基本法律。这说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也要受合同法的调整。
其次,物权法过于僵化的缺陷需要灵活的合同制度来缓解。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差距甚大,地方条件的差异导致村民间的
利益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制度创新。不同的承包经营合同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地域,几乎没有一种模式是能够有效地适用于全国各个千差万别的地区的。在经济比较贫困的地区,土地对村民的价值相对较大,村民对土地要求公平均分的愿望就较强烈,均田制就较符合人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第二、第三产业更吸引农村的劳动力,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功能退化,村民更关注土地制度的效率问题,因而规模经营就比较适宜,承包方享有更多的权利,比如抵押权、转让权和转包权。各种模式的承包合同制度中承包方实际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不尽相同,对它们的共性纳入到物权法中是可行的,但是对于各自不同的部分应由合同制度来调整。